
逃婚路上捡个夫,竟是当朝摄政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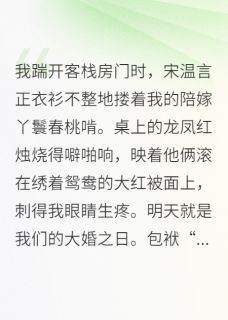
作者:爷不喜欢画饼
分类:短篇
状态:已完结
时间:2025-07-05 14:42
我踹开客栈房门时,宋温言正衣衫不整地搂着我的陪嫁丫鬟春桃啃。
桌上的龙凤红烛烧得噼啪响,映着他俩滚在绣着鸳鸯的大红被面上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
明天就是我们的大婚之日。包袱“咚”地砸在地上,我跑了一路攒的私房银子撒了一地。
宋温言像被火燎了**的猴子,猛地弹起来,抓起外袍就往身上裹,声音都劈了叉:“阿绝?
!你…你怎么来了?你不是该在沈府待嫁吗?”春桃尖叫一声,扯过被子把自己裹成个蚕蛹,
只露出一双湿漉漉、满是惊恐的眼睛,看着我,又看看宋温言。
我盯着宋温言那张一向温润、此刻却写满慌乱和心虚的脸。心口那块地方,
像是被寒冬腊月的冰坨子狠狠砸了一下,又冷又硬,碎得生疼。原来他这些日子的忙碌,
所谓的“婚前不宜相见”,都是在忙着睡我的丫鬟。“待嫁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
冷得像结了冰碴子,“等着看我的好夫君和我的好丫鬟,在我的嫁妆铺盖上滚成一团,
再喝你们的喜酒吗?”我一步步走过去,靴子踩在散落的碎银上,发出咯吱的轻响。
宋温言下意识后退半步,脸上挤出惯常的、用来哄骗我的温柔:“阿绝,
你听我解释…不是你想的那样…是春桃她…她勾引我!对,是她不知廉耻!”“公子!
”春桃不敢置信地哭喊出来。“闭嘴!”宋温言厉声呵斥她,转头又对我赔笑,
伸手想来拉我,“阿绝,我心里只有你,明日大婚照旧,我们…”我猛地扬手。“啪!
”清脆响亮的耳光,狠狠扇在他那张虚伪的脸上。力道之大,打得他头都偏了过去,
白皙的脸上迅速浮起五个清晰的指印。世界安静了。宋温言捂着脸,震惊地看着我,
仿佛第一次认识我。春桃吓得连哭都忘了。我弯腰,捡起地上那个沉甸甸的包袱,抖开。
里面没有一件衣物,只有厚厚一叠纸。我抽出最上面那张,
鲜红的官印刺目——那是我们的婚书。“宋温言,”我看着他,一字一句,清晰无比,
“你我自幼定亲,我沈绝自认从未亏欠于你。”“你要开铺子,
我拿自己的体己银子给你当本钱。”“你娘病重,我三天三夜不合眼在床前侍奉汤药。
”“你说想专心举业,我顶着爹娘的骂声,硬是拖到十八才肯与你议婚期。”我每说一句,
宋温言的脸色就白一分。“可你呢?”我捏着那张婚书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,
“你拿我的银子养外室?还是我的陪嫁丫鬟?在我为我们的婚事绣嫁衣的时候,
你就躺在这里,抱着她,用我的嫁妆银子开的房?”我逼近一步,
宋温言竟被我的气势慑得又退了一步。“沈家是商贾,配不上你宋秀才的清贵,我知道。
”我扯了扯嘴角,那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,“可我没想到,你连这点脸面都不要了。
婚前偷腥,偷的还是我的人,用我的钱?
”积压了多年的委屈、隐忍、还有此刻被彻底背叛的愤怒,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。“宋温言,
你真让我恶心!”话音未落,我双手抓住那张刺眼的婚书。
“嘶啦——”脆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惊心。鲜红的官印被从中撕裂。
“嘶啦——嘶啦——”我面无表情,一下,又一下,将那张代表我前半生期盼和束缚的纸,
撕得粉碎。纸屑像红色的雪片,纷纷扬扬,洒了宋温言满头满脸。他呆若木鸡。
我最后看了他一眼,那眼神大概冷得像冰窟:“从今往后,我沈绝与你宋温言,恩断义绝。
婚约作废,男婚女嫁,各不相干!”说完,我弯腰,
一把抄起地上散落的、原本打算用来逃婚的银子,胡乱塞进包袱,转身就走。“沈绝!
你给我站住!”宋温言如梦初醒,气急败坏地冲过来想抓我,“婚书岂是你说撕就撕的!
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由不得你胡闹!明日大婚照旧!你休想…”“滚!
”我反手抽出藏在靴筒里的匕首,寒光一闪,直直指向他。那是我爹怕我路上不安全,
硬塞给我的。宋温言吓得猛地刹住脚,脸色煞白地看着我手中闪着冷光的利器,嘴唇哆嗦着,
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“再敢碰我一下,”我盯着他的眼睛,声音不大,
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,“我就剁了你的爪子。我说到做到。”他僵在原地,像一尊泥塑。
我收回匕首,不再看他一眼,撞开挡路的他,大步冲出了这个令人作呕的房间。
身后传来宋温言歇斯底里的咆哮和春桃尖利的哭声。雨下得很大。豆大的雨点砸在脸上,
生疼,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衫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在城外的泥泞小路上,
包袱紧紧抱在怀里,里面是我全部的身家——那些散碎的银子和几件值钱首饰。
脑子里乱哄哄的,只有一个念头:跑!离开这里!离开那个虚伪恶心的男人!
离开那场即将成为全城笑柄的婚礼!去哪里?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我沈绝,
宁死也不做那对狗男女的遮羞布!雨幕厚重,天地间一片混沌。山路崎岖湿滑,
好几次我差点摔倒。不知跑了多久,体力快要耗尽,肺部**辣地疼。
就在我扶着路边一棵歪脖子老树喘气时,脚下猛地一滑!“啊!”整个人失去平衡,
顺着一个陡坡就滚了下去。泥水、碎石、枯枝烂叶糊了满头满脸。天旋地转。
最后“砰”的一声闷响,后背撞上什么东西,总算停了下来。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,
疼得我眼前发黑。我龇牙咧嘴地撑起身,抹掉糊住眼睛的泥水。借着微弱的天光,
我看清了垫在我身下的“东西”。是个人!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男人!他仰面躺在泥水里,
一动不动,脸色惨白得像死人,嘴唇毫无血色。胸口处深色的衣料被雨水浸透,
颜色深得发黑,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死人?我头皮一麻,吓得魂飞魄散,
手脚并用地就想爬起来跑。“咳…咳咳…”极其微弱,几乎被雨声淹没的咳嗽声响起。
他还活着!我动作顿住,惊疑不定地看着他。雨水冲刷着他脸上和身上的泥污,
露出一张极其年轻、也极其英俊的脸,即使苍白如纸,也难掩那种刀削斧凿般的轮廓。
只是眉头紧紧锁着,似乎在忍受巨大的痛苦。他伤得很重,
胸口的伤还在缓慢地往外渗着血水,被雨水冲淡,蜿蜒流进泥里。救,还是不救?
我身上麻烦够多了,逃婚,撕毁婚书,
还带着匕首伤了宋温言……要是再惹上人命官司……可是…把他丢在这荒山野岭的雨夜里,
他必死无疑。他看起来,也不像坏人?至少那张脸,比宋温言那个伪君子顺眼多了。
我还在天人交战,地上的人又痛苦地闷哼了一声,眼皮艰难地掀开一条缝。那眼神,
黑沉沉的,像深不见底的寒潭,带着濒死的茫然和一丝本能的警惕,虚弱地看了我一眼,
随即又无力地阖上。就这一眼,让我心里那点犹豫瞬间没了。算了!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!
我咬咬牙,费力地把他沉重的身体半拖半抱起来,环顾四周。雨太大,天也快黑了,
必须先找个地方避雨,处理他的伤。运气不算太坏,
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被藤蔓半遮掩着的山洞。洞口不大,里面却还算干燥,
似乎是什么猎户歇脚的地方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几乎是连滚带爬,
才把这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重伤男人拖进了山洞。洞里有前人留下的干草垛,
还有半堆没烧完的柴禾。我把他小心地安置在干草垛上。解开他湿透的深色外袍,
里面的白色中衣已经被血浸透了一大片,黏糊糊地贴在胸口。伤口在左胸偏上的位置,
一道狰狞的裂口,皮肉外翻,还在渗血。万幸,似乎没伤到心脏要害,但失血过多,
加上淋雨,情况非常危险。我包袱里带着应急的金疮药,是开药铺的三叔硬塞给我的,
说是姑娘家出门在外以防万一。还有一壶没喝完的烧刀子。我撕下自己还算干净的里衣下摆,
用烧刀子浸湿,咬着牙,一点点清理他伤口周围的泥污和血痂。
他痛得浑身都在无意识地抽搐,牙关紧咬,发出压抑的闷哼,冷汗混着雨水从额角滚落。
“忍着点…很快就好…”我也不知道是在安慰他还是安慰自己,手抖得厉害。清理干净,
撒上厚厚的金疮药粉,用撕成条的布条紧紧包扎起来。做完这一切,我累得几乎虚脱,
靠着冰冷的石壁喘气。洞里光线昏暗,只有洞口透进来的微弱天光。我摸索着,
用火折子点燃了那堆柴禾。橘红色的火焰跳跃起来,驱散了洞内的阴冷和黑暗,
也带来了些许暖意。火光映在那张昏迷的脸上,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浓密的阴影,
鼻梁挺直,薄唇紧抿。即使昏迷着,眉宇间也凝着一股化不开的沉郁和…上位者的威严?
我摇摇头,甩掉这荒谬的念头。大概是累糊涂了。添了几根柴,让火烧得更旺些。
我又摸了摸他的额头,烫得吓人!伤口感染,加上淋雨,高烧是必然的。我解开包袱,
里面除了银钱和药,还有一小包用油纸仔细包好的饴糖,是我准备路上解闷的。
我掰开一小块,又倒了些烧刀子,兑了点雨水,想给他灌下去补充点体力退烧。
捏开他的下颌,小心翼翼地把糖水灌进去。他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,咽下去一些,
更多的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。“喂!你争气点啊!我好不容易把你拖进来!”我又急又无奈,
用手背胡乱擦掉他下巴上的水渍,“药也上了,火也生了,你可别死在我面前!
我沈绝刚甩掉一个晦气的未婚夫,不想再沾上人命官司!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念叨起了作用,
还是糖水真的补充了点能量。他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点点。我松了口气,坐在火堆旁,
抱着膝盖,看着跳跃的火焰发呆。一天之内,翻天覆地。从待嫁新娘,变成逃婚弃妇,
还在荒山野岭捡了个半死不活的男人。这都叫什么事儿!“水…”极其沙哑微弱的声音响起。
我猛地回神,凑过去:“你醒了?”他眼睛半睁着,眼神涣散,没有焦距,
显然还没完全清醒,只是本能地渴求:“…水…”我赶紧把水囊凑到他嘴边,
小心地喂他喝了几口。清凉的雨水似乎让他恢复了一丝清明,他费力地转动眼珠,
目光终于聚焦在我脸上。那眼神,带着审视、警惕,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。“你是谁?
”他开口,声音依旧嘶哑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。“我?”我指了指自己鼻子,
没好气,“你的救命恩人!要不是我,你早就在外面淋雨流血变成孤魂野鬼了!
”他沉默了一下,似乎在回忆,目光扫过自己包扎好的胸口,
又看了看燃烧的火堆和洞口的雨幕。“…多谢。”声音低沉,没什么温度。“谢就不用了,
”我摆摆手,“你叫什么?怎么伤成这样?被仇家追杀?还是遇到山贼了?”他垂下眼帘,
浓密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情绪,声音平淡无波:“霍醒。做点小买卖,路上遇到劫道的了。
”霍醒?这名字…有点怪。醒?他现在半死不活的,哪里醒了?“小买卖?
”我狐疑地打量他。虽然衣服脏污破损,但那料子,绝不是普通商贩能穿的起的细棉,
更像是某种低调奢华的锦缎。而且他刚才看人的眼神,那种无形的压迫感…“嗯。
”他应了一声,不再多说,闭上眼睛,一副拒绝交谈、专心养伤的样子。行吧。萍水相逢,
他不想说,我也懒得追问。我自己还一**烂账呢。“沈绝。”我还是报上了名字,
“逃婚出来的。”他闭着的眼睛似乎动了一下,没睁开,也没再说话。
山洞里只剩下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洞外哗哗的雨声。一夜无话。天快亮时,雨终于停了。
霍醒的高烧退了点,但人依旧虚弱,脸色苍白得像纸,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“喂,霍醒,
”我戳了戳他,“天亮了,我得走了。你自己…能行吗?”他睁开眼,
眼神比昨晚清明了一些,看着我:“你要去哪?”“不知道,”我耸耸肩,语气尽量轻松,
“天大地大,总有我沈绝的容身之处。先找个城镇落脚吧。”他沉默了片刻,
似乎在权衡什么,然后开口,声音依旧虚弱,却带着一种奇怪的笃定:“我伤重,无法独行。
你救我,算是我的恩人。不如…你我同行一段?待我伤势稍缓,必有重谢。”重谢?
我眼睛亮了亮。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钱!逃婚出来,虽然带了点体己,但坐吃山空不是办法。
他看起来像个有钱的主儿……“你能给多少?”我直白地问。
他似乎被我如此直白的问法噎了一下,
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笑意:“不会让你吃亏。”“成交!
”我爽快地拍板。反正我也没明确目的地,带着个重伤的“钱袋子”,总比一个人瞎闯强。
我出去找了些野果,又用皮囊装了干净的雨水。回到山洞,霍醒靠着石壁坐着,闭目养神。
脸色还是难看,但精神似乎好了一点点。“吃点东西,我们得走了。这地方不能久留。
”我把野果递给他。他接过,动作缓慢地吃着,举手投足间,总有种刻在骨子里的…优雅?
我甩甩头,一定是错觉。一个被劫道的小商人,哪来那么多讲究。简单收拾了一下,
我架起他的胳膊,让他大半重量靠在我身上。他很高,很沉。我咬着牙,使出浑身力气,
才勉强支撑着他,一步一步,艰难地挪出了山洞。雨后初晴,山林里空气清新。
我们走得很慢。霍醒大部分时间沉默,偶尔问几句无关紧要的话,比如现在是哪年哪月,
这附近最大的城镇是哪里。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。“沈姑娘为何逃婚?”他忽然问,
语气平淡,听不出情绪。我脚步顿了一下,随即自嘲地笑了笑:“撞见我的好未婚夫,
搂着我的陪嫁丫鬟,滚在我的嫁妆被面上,就在我们大婚的前一天。不逃,难道留着过年?
”霍醒侧头看了我一眼,眼神有些深:“撕了婚书?”“嗯,”我点头,语气带着一股狠劲,
“撕得粉碎!还给了那伪君子一巴掌!”他似乎轻轻哼了一声,像是笑,
又不像:“倒是个烈性子。”“不然呢?忍气吞声,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恶心我?
”我嗤笑,“我沈绝没那么贱骨头!”他没再说话。沉默地走了大半天,日头偏西时,
终于看到了官道。也看到了官道旁挑着“茶”字幡子的简陋茶棚。我如蒙大赦,
架着霍醒走过去,把他安置在茶棚角落的长条凳上。“累死我了…”我揉着酸痛的肩膀,
招呼老板,“老板,来壶热茶,再上几个馒头!要热乎的!”老板应了一声。我刚喘了口气,
准备坐下。“沈绝?!”一个尖利、熟悉、带着震惊和愤怒的声音,像淬了毒的针,
猛地扎进我的耳朵。我浑身一僵,猛地转头。茶棚入口处,站着三个人。为首的,
正是宋温言!他脸上还带着点没消的红肿指印,头发有些凌乱,一身锦袍也沾了泥点,
显然是一路追出来的。此刻他正死死地盯着我,眼神像是要吃人。
他身后跟着两个家丁打扮的壮汉,一脸凶相。真是冤家路窄!我瞬间头皮发麻,
下意识地挡在了霍醒身前。霍醒原本闭目养神,此刻也缓缓睁开了眼,
目光平静地扫过宋温言一行人,最后落在我紧绷的脊背上。“沈绝!你好大的胆子!
”宋温言几步冲过来,指着我的鼻子,气得浑身发抖,“撕毁婚书,持刀行凶!
还敢带着个野男人私奔?!”“野男人”三个字像耳光一样抽过来。
茶棚里零星的几个客人纷纷侧目。“你嘴巴放干净点!”我怒火中烧,毫不畏惧地顶回去,
“宋温言,婚书已撕,你我毫无瓜葛!我沈绝爱跟谁走就跟谁走,轮不到你指手画脚!
带着你的狗,滚!”“毫无瓜葛?”宋温言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眼神怨毒,“父母之命,
媒妁之言!岂是你说撕就撕的?你生是我宋家的人,死是我宋家的鬼!想跟这个野男人跑?
做梦!”他阴冷的目光越过我,落在靠坐在那里、脸色苍白的霍醒身上,充满了鄙夷和嫉恨。
“给我把这个不知廉耻的**拿下!把这个奸夫也给我打断腿!
”宋温言厉声对身后的家丁吼道。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丁立刻撸起袖子朝我扑来!“谁敢动她!
”一声低沉冰冷的断喝,如同寒冰乍破,陡然在小小的茶棚里炸开!声音不大,
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和凛冽的杀意,瞬间让那两个扑过来的家丁动作一僵,
硬生生刹住了脚步。是霍醒!他不知何时已经扶着桌子站了起来。脸色依旧苍白得近乎透明,
身形也因为重伤和虚弱而微微晃动,全靠一只手撑着桌面才勉强站稳。可他的眼神,
却锐利得惊人!那双深邃的黑眸,此刻像淬了寒冰的利刃,冷冷地扫过宋温言和那两个家丁,
带着一种居高临下、视他们如蝼蚁般的漠然。被他目光扫到的人,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。
宋温言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震得一愣,随即恼羞成怒:“你算什么东西?
一个快死的病秧子,也敢管我宋家的家事?给我上!连他一起打!”家丁被主人一吼,
再次凶相毕露,朝霍醒扑去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!霍醒重伤在身,连站都勉强,
怎么可能是两个壮汉的对手?就在一个家丁的拳头即将砸到霍醒面门时——霍醒动了!
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!他甚至没有离开支撑桌面的手,只是上身极其灵活地一侧,
那只家丁的拳头便擦着他的脸颊落空。与此同时,霍醒那只撑着桌面的手闪电般探出,
不是攻击,而是极其精准地在那家丁扑空后露出的肋下某处,屈指一弹!动作轻描淡写,
甚至带着一种病弱的优雅。“呃啊——!”那壮硕的家丁却像被千斤重锤砸中,
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,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骨头,轰然倒地,蜷缩成一团,浑身抽搐,
口吐白沫,连惨叫都发不出来了!另一个家丁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,
硬生生刹住脚步,惊恐地看着地上瞬间失去战斗力的同伴,
《逃婚路上捡个夫,竟是当朝摄政王》的章节设计引人入胜,让人难以割舍。男女主角的曲折传奇爱情故事令人回味无穷,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。
爷不喜欢画饼的作品总是令我惊喜。《逃婚路上捡个夫,竟是当朝摄政王》的故事情节特别吸引人,跌宕起伏,让我爱不释手。
《逃婚路上捡个夫,竟是当朝摄政王》以其精彩的情节和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吸引了读者的目光。每个章节都扣人心弦,故事中男女主角之间曲折传奇的爱情故事令人深思。在众多小说中,这是最好的之一。
《逃婚路上捡个夫,竟是当朝摄政王》的章节设计引人入胜,让人难以割舍。男女主角的曲折传奇爱情故事令人回味无穷,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