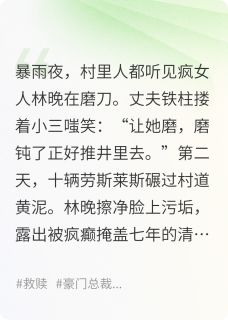暴雨夜,村里人都听见疯女人林晚在磨刀。丈夫铁柱搂着小三嗤笑:“让她磨,
磨钝了正好推井里去。”第二天,十辆劳斯莱斯碾过村道黄泥。林晚擦净脸上污垢,
露出被疯癫掩盖七年的清冷面容。“王铁柱,你推我爹下井那天,我清醒了。”祠堂里,
她甩出亲子鉴定:“你养了七年的儿子,是我的血脉。”“至于你亲生的?”她轻笑,
“早被你们亲手丢进后山喂狼了。”百亿买下整座村庄,她指着丈夫和小三:“这块地,
以后叫化粪池。”---噼啪!惨白的电光撕裂浓墨般的夜幕,
将院中那佝偻磨刀的身影瞬间拓印在湿漉漉的泥地上,又猛地被黑暗吞噬。紧接着,
一声撼动房梁的炸雷轰然滚过天际,震得窗棂嗡嗡作响,仿佛整个王家洼都在瑟瑟发抖。雨,
瓢泼而下。冰冷的雨水砸在院角的破瓦罐上,发出单调而空洞的“咚咚”声,
如同催命的鼓点。屋檐下淌下的水线连成一片浑浊的珠帘,隔绝了院内院外。
就在这片震耳欲聋的喧嚣与令人窒息的黑暗里,只有一种声音顽强地穿透雨幕,
钻进每一个蜷缩在热炕头上、却又竖起耳朵偷听的村民耳中。
嗤啦——嗤啦——那是刀刃在粗粝的磨刀石上反复刮擦的声音。单调,刺耳,
带着一种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质感,一下,又一下,执着得近乎疯狂。每一次拖动,
都像是钝器刮在紧绷的神经上。“啧,又来了!这疯婆娘,没个安生时候!”西厢房里,
王铁柱光着膀子,趿拉着鞋走到窗边,粗鲁地“哗啦”一声拉开半边窗子,探出脑袋,
对着院子里那个模糊的身影不耐烦地吼了一嗓子,“林晚!大半夜的号丧啊!
还让不让人睡了!”回应他的,只有更响亮、更急促的“嗤啦——嗤啦——”声。
那磨刀的身影仿佛凝固成了雨夜的一部分,对男人的呵斥充耳不闻。“哼!
”王铁柱重重啐了一口,唾沫星子混着雨水溅落窗台。他猛地缩回头,用力关上窗户,
隔绝了那恼人的噪音和冷风。炕上,一个穿着碎花吊带睡衣的女人慵懒地支起身子,
正是张红霞。她撇撇嘴,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和讥诮,伸手把王铁柱拉回暖烘烘的被窝。
“管她呢,铁柱哥,”张红霞的声音又软又腻,带着一股刻意的娇媚,
手指在男人厚实的胸膛上画着圈,“一个疯子,磨刀?呵,让她磨呗!磨得越起劲越好,
磨钝了,正好!省得我们费劲,直接推进井里,一了百了!”她凑近王铁柱耳边,
压低了声音,语气却带着一种恶毒的兴奋:“后山那口枯井,井盖我都看过了,锈死了,
焊得死死的!她就算真疯了往里跳,也甭想再爬出来!”黑暗中,她的眼睛闪着幽冷的光,
像伺机而动的毒蛇。王铁柱嘿嘿一笑,粗糙的大手在张红霞滑腻的肩头用力揉捏着,
仿佛那不是人,而是一件趁手的物件。“还是霞妹你想得周全!”他嗓门粗嘎,
带着纵欲后的满足和一丝残忍的得意,“那老东西当初不识抬举,
非要把那点破家底留给这疯婆娘,活该他先下去探路!这疯婆子,也早该去陪她死鬼爹了!
省得碍眼!”窗外的磨刀声,在密集的雨点敲打声中,依旧固执地响着。
嗤啦——嗤啦——像是一首无人能懂、却充满不祥预感的镇魂曲,
固执地盘旋在王家洼这个风雨飘摇的夜晚。暴雨肆虐了一夜,直到天色微明,
才渐渐显出疲态,收起了它那狂暴的鞭子,只剩下淅淅沥沥的余威,
敲打着残破的屋檐和泥泞的地面。王家洼湿漉漉地醒来,
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味和草木被蹂躏后的腐败气息。王铁柱打着哈欠,
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堂屋门。一股带着凉意的湿气扑面而来,
他下意识地朝院子角落瞥去——昨晚那个磨刀的位置空空如也。
只有那块被雨水冲刷得格外干净的磨刀石,孤零零地躺在泥水里,反射着灰白的天光。“呸!
”他朝着那方向吐了口浓痰,心里说不出的烦躁和一丝被忽略的恼火。疯婆娘人呢?
该不会真发疯跑出去了?念头一闪而过,随即又被张红霞在屋里娇声的催促淹没:“铁柱哥,
快进来呀,外头冷!”他正要转身,一阵不同寻常的沉闷震动,隐隐从村口方向传来。
那声音起初极细微,混杂在雨滴声里几乎难以分辨。但很快,
它就变得清晰、稳定、富有压迫感。不是拖拉机的突突声,也不是农用三轮的颠簸响动,
而是一种低沉、浑厚、带着金属质感的嗡鸣,仿佛大地深处传来的闷鼓。
王铁柱的脚步顿住了,疑惑地竖起耳朵。这动静……不对劲!震动感越来越强,
连脚下湿滑的地面都似乎有了轻微的颤抖。王家洼狭窄、泥泞、坑洼不平的主道上,
平日连拖拉机开进来都得小心翼翼。是什么东西,能发出这样沉重的、碾压一切的声音?
好奇心和某种莫名的不安驱使着他,王铁柱忘了屋里的张红霞,也忘了消失的林晚,
鬼使神差地趿拉着沾满黄泥的破胶鞋,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村口方向走去。不只是他。
村道两旁低矮破旧的院门,吱呀吱呀地打开了一条条缝隙。
一张张睡眼惺忪、布满皱纹的脸探了出来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带着同样的惊疑和茫然,
望向那声音的来源。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,已经稀稀拉拉站了十几个被惊醒的村民。
浑浊的泥水顺着他们破旧的裤腿往下淌,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,
朝着村外那条被雨水泡得稀烂、黄泥汤横流的土路尽头张望。震动越来越近,
嗡鸣声变成了低沉的咆哮,震得人胸腔发闷。来了!一片令人窒息的、泛着幽暗光泽的黑色,
沉稳而不可阻挡地碾过土路尽头那道低矮的山梁,闯入所有人的视野。一辆,两辆,
三辆……整整十辆!车身线条流畅得如同刀锋劈开雨幕,庞大而低伏,
带着一种与这片贫瘠土地格格不入的冷硬与奢华。
那标志性的矩形格栅和矗立在车头的欢庆女神立标,在灰暗的晨光里闪烁着拒人千里的寒光。
巨大的轮胎毫不留情地碾过坑洼,溅起浑浊的泥浆,
泼洒在路旁枯黄的野草和目瞪口呆的村民身上,留下肮脏的斑点。
“老天爷……”有人倒吸一口凉气,声音卡在喉咙里。“这……这啥车?咋恁大?恁多?
”另一个老汉揉着眼睛,怀疑自己还没睡醒。“劳……劳斯莱斯!我在城里打工时,
工头指给我看过!一辆就值老鼻子钱了!这……这十辆?!
”一个稍微见过点世面的年轻人声音都变了调,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“娘咧!
开到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啥?”人群骚动起来,恐惧压倒了好奇。
这种传说中的巨兽突然降临穷山沟,带来的不是惊喜,
而是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、被未知力量碾压的恐慌。车队没有理会路边惊惧的村民,
保持着绝对沉默的威严,像一支黑色的钢铁洪流,沉稳地驶入王家洼狭窄的村道。
沉重的车身压得泥浆翻涌,发出令人牙酸的“咕叽”声。它们的目标明确,
径直朝着村子深处,王铁柱家那破败院子的方向驶去。“坏了!冲铁柱家去的!
”有人失声惊呼。王铁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,
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,几乎停止了跳动。他脑子里一片空白,
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:完了!出大事了!他下意识地转身就想往家里跑,
两条腿却像灌满了铅,沉重得抬不起来,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钢铁巨兽组成的阴影,
一寸寸逼近他那破败的家门。“吱嘎——”刺耳的刹车声在泥泞中响起,
十辆劳斯莱斯如同训练有素的士兵,在王铁柱家那扇歪斜、漆皮剥落的院门前,
排成一道沉默而极具压迫感的黑色钢铁屏障。车门几乎在同一时间打开。动作整齐划一。
十名身着笔挺黑色西装、戴着墨镜、身形矫健的保镖利落地跃下车。
雨水打在他们一丝不苟的肩头,墨镜遮住了眼神,只留下冰冷坚硬的下颌线条。
他们沉默地分散开,如同磐石般钉在泥泞的地面上,
隔绝了所有窥探的目光和试图靠近的村民,形成一道无形的、令人窒息的警戒圈。
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只有雨滴打在豪车光洁顶棚和保镖们肩头发出的轻微声响,
以及村民们压抑到极致的、粗重的呼吸声。王铁柱家那扇破旧的院门,发出不堪重负的**,
被人从里面缓缓拉开。吱呀——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内。刹那间,所有看清那张脸的人,
都如同被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中了心脏,大脑一片空白,连呼吸都忘了!林晚?!
是那个疯女人林晚!但她……她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?!
她身上那件穿了不知多少年、早已看不出颜色和形状、沾满泥污和秽物的破烂棉袄不见了。
取而代之的,是一身剪裁极致利落、线条冷硬的银灰色套装,质地精良,
在晦暗的雨幕中流淌着内敛而冰冷的光泽。那颜色,像淬了寒冰的刀刃。
更令人魂飞魄散的是她的脸!
那张总是糊满污垢、头发板结打绺、眼神浑浊呆滞、只会傻笑或尖叫的脸庞,
此刻被擦拭得干干净净,露出底下欺霜赛雪的肌肤。雨水顺着她光洁的额头滑落,
沿着清瘦却线条分明的下颌滴落。湿透的乌黑长发不再疯癫地纠缠,
而是被一丝不苟地梳理到脑后,露出饱满而冷峻的额头。最摄人心魄的是她的眼睛。
不再是空洞的茫然或狂乱的浑浊,而是一双深不见底的寒潭。眼瞳极黑,极冷,
像淬了千年的寒冰,又像是蕴藏着即将爆发的熔岩。
那目光平静地扫过院外围得水泄不通、如同泥塑木雕般的村民,
扫过呆若木鸡、脸上血色瞬间褪尽的王铁柱,最后,精准地落在了他身后堂屋门口,
个穿着吊带睡衣、被眼前景象惊得忘记寒冷、只顾张着嘴、眼珠子几乎瞪出来的张红霞身上。
那目光没有愤怒,没有怨恨,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、彻骨的漠然,
仿佛在看脚下两只微不足道的蝼蚁。时间在那一秒被冻结了。
整个世界只剩下雨水滴落的声音,以及无数颗心脏因过度震惊而疯狂擂动的轰鸣。
王铁柱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,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怪响,像是破风箱在漏气。
他死死地盯着林晚,那张他看了七年、厌恶了七年、早已刻入骨髓的疯妇的脸,
此刻却陌生得让他浑身血液都冻成了冰渣。一股巨大的、灭顶的恐惧像冰冷的毒蛇,
瞬间缠紧了他的心脏,越收越紧。张红霞更是不堪,她像是骤然被抽掉了全身骨头,
软软地顺着门框滑坐到冰冷的泥地上,吊带睡衣沾满了污浊的泥水也浑然不觉。她仰着头,
瞳孔涣散,只剩下无意识的颤抖,仿佛看到了从地狱爬回来的索命恶鬼。
林晚的目光只在两人身上停留了短暂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瞬,便移开了。她微微侧过头,
声音不高,却清晰地穿透雨幕,带着一种久居上位、不容置疑的冷冽,
吩咐身旁一位面容严肃、提着精致公文包的中年男人:“陈律师,开始吧。”“是,林董。
”陈律师微微躬身,姿态恭敬无比。他打开公文包,取出一份文件,向前一步,
目光锐利地扫向魂不附体的王铁柱,声音洪亮而刻板:“王铁柱先生,张红霞女士。
根据林晚女士的指示及林氏集团法务部的授权,现正式通知二位:林晚女士名下,
位于王家洼村西头、原属林晚女士父亲林国栋先生名下的祖宅及连带土地,
其所有权和使用权,即刻收回。限你们十分钟内,清空个人物品,离开该处房产。
”“什……什么?”王铁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,猛地跳了起来,
脸上瞬间涌上猪肝般的紫红色,恐惧被巨大的荒谬感和被冒犯的暴怒冲散了一些,“收回?
那是我的房子!我老丈人……林国栋死了!我是他女婿!那房子就该是我的!还有地!
她一个疯子……她懂个屁!”他指着林晚,手指因为激动和恐惧剧烈地颤抖着,唾沫横飞,
试图用音量掩盖内心的恐慌。陈律师面无表情,声音冷得像冰:“王铁柱先生,
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林国栋先生生前立有有效遗嘱,其名下所有不动产及动产,
唯一继承人为其女林晚女士。该遗嘱经公证处公证,具有完全法律效力。
至于林晚女士的精神状态,”他微微一顿,目光转向林晚,带着绝对的尊重,
“权威医疗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,林晚女士意识清醒,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过去七年的一切,另有公断。”他抬腕看了看价值不菲的手表:“现在,计时开始。
九分五十秒。”“你放屁!她是疯子!全村都知道她是疯子!”王铁柱彻底慌了,
口不择言地嘶吼起来,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困兽,试图冲上去抢夺那份文件,
却被两名动作迅捷如豹的保镖轻而易举地反剪双臂,死死按在冰冷的泥水里。
他徒劳地挣扎着,昂贵的西装瞬间被黄泥浸透,狼狈不堪。“铁柱哥!
”张红霞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,连滚爬爬地想扑过去,却被另一个保镖冰冷的眼神钉在原地,
只剩下筛糠般的颤抖。林晚自始至终,没有再看他们一眼。她微微抬了抬下颌,
目光投向村子中央,那座青砖黑瓦、象征着宗族最高权力的古老祠堂。风雨中,
祠堂的飞檐沉默地指向铅灰色的天空,如同一个垂暮的巨人。“去祠堂。”她的声音不大,
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,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决断。黑色的人潮,
沉默的钢铁巨兽,簇拥着那个银灰色、如同出鞘利剑般的身影,碾过泥泞,
朝着祠堂方向缓缓移动。所过之处,围观的村民如同被无形的潮水分开,下意识地后退,
让出一条通路。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惊惧、茫然和无法理解。那磨刀的疯女人,
那被他们鄙夷、嘲弄、甚至暗自盼着她消失的林晚,怎么会变成这样?
这从天而降的财富和力量,又是怎么回事?祠堂厚重的木门被无声地推开。里面光线昏暗,
弥漫着陈年香烛和木头腐朽的混合气味。供奉着密密麻麻祖宗牌位的神龛前,
几张老旧的八仙桌被临时拼在一起,权当讲台。林晚在陈律师和几名核心保镖的簇拥下,
径直走到最前方。她没有看那些惊疑不定、随后跟进来挤满了祠堂大门的村民,
也没有看被保镖粗暴拖拽进来、如同死狗般瘫在地上的王铁柱和张红霞。她的目光,
平静地落在祠堂正中央悬挂的一块巨大、古旧的匾额上,
上面是四个褪了色的金漆大字——“敦亲睦族”。雨点密集地敲打着祠堂古老的瓦片,
噼啪作响,像无数双焦躁的手在叩问。祠堂内光线昏暗,空气凝滞得如同胶水,
混合着陈腐的香烛味、泥土腥气和人群散发的惶恐汗味。密密麻麻挤在门口和天井里的村民,
连大气都不敢喘,
所有的目光都死死钉在那个站在神龛前、一身银灰、如同寒冰铸就的身影上。
王铁柱和张红霞被保镖按着,跪在冰冷的青砖地上。王铁柱还在徒劳地挣扎,
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低吼,张红霞则只剩下绝望的呜咽,身体抖得如同风中的落叶。
林晚终于缓缓转过身。祠堂内微弱的光线勾勒着她清瘦而冰冷的侧影,
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扫过下方一张张惊惧茫然的脸,最后,
如同冰锥般刺向地上那对狼狈不堪的男女。“王铁柱。”她的声音在空旷的祠堂里响起,
不高,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,每一个字都清晰地敲打在众人的心坎上,冰冷彻骨,
“七年了。这七年来,你睡在我的床上,用着我爹留下的钱,养着你的姘头,
还要每天骂我是疯子,盼着我死。”她的目光转向张红霞,
那眼神里的寒意几乎要凝成实质:“张红霞,你鸠占鹊巢,踩着我爹的尸骨,用着我的家产,
还要一口一个‘疯婆子’地叫我,连你生的野种,都敢腆着脸让我这个‘疯子’帮你带?
”祠堂里死一般的寂静,只有她冰冷的声音在回荡,字字如刀。林晚微微停顿了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