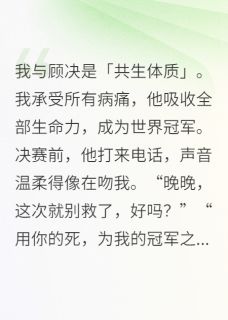我与顾决是「共生体质」。我承受所有病痛,他吸收全部生命力,成为世界冠军。决赛前,
他打来电话,声音温柔得像在吻我。“晚晚,这次就别救了,好吗?”“用你的死,
为我的冠军之路,画上一个最深情的句号。”我感受着体内骨头寸寸碎裂的剧痛,笑了。
“好啊,顾决,我成全你。”电话那头,他献祭爱人换来的平静,
被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。1.我和顾决,是世间罕见的“共生体质”。
这是他告诉全世界的浪漫版本。这个版本里,我们是青梅竹马,从出生起就命运相连。
我生来便要承受家族遗传病的所有痛苦,而他,则能奇迹般地吸收我的生命力,
享受双倍的健康与快乐。我是他命中注定的劫,他是我无以为报的缘。
为了让他实现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,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“续命良药”,
用我日渐衰败的身体,供养他日益强健的体魄。二十年来,我每一次病发,
都对应着他的一次突破。我第一次因为骨痛昏厥,他拿下了全国青少年游泳比赛的冠军。
我第一次被下病危通知书,他在亚运会上一战成名。我每一次被推进ICU抢救,
都成了他赛前最好的“**”,让他能以最完美的姿态,站上最高的领奖台。而他,
也确实给了我“回报”。他把我从那个破旧的小城带到繁华的都市,
让我住进顶级的疗养病房,给了我看似优渥的生活。代价是,我成了一个符号。
一个代表着“病弱”、“拖累”、“牺牲”的符号。在媒体面前,
他是那个对病入膏肓的爱人不离不弃的“情圣”。我的每一次病容憔悴,
都成了他坚韧深情人设最扎实的背景板。他越是成功,我的存在就越能反衬出他的伟大。
全世界都在赞美他,同情我。我以为,我的牺牲,能换来他一世的荣光和我们永恒的陪伴。
直到他站上世界之巅,回过头,却想亲手将我推入深渊。2人心,
是比遗传病更难预测的东西。当顾决的光芒越来越盛,他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
不再是年少时的依赖与心疼,而是一种混杂着怜悯、不耐与……嫌弃的复杂情绪。
他开始在媒体面前,将我的病描绘成他奋斗路上的悲情注脚。“如果没有晚晚,
我或许会更轻松,但我从不后悔。”“每次看到她痛苦,我都恨不得替她承受,
这份痛苦也化作了我前进的动力。”他说得越多,得到的同情和赞誉就越多。而我,
从他的爱人,渐渐变成了他完美人设的一部分,一个用来证明他深情的、活生生的道具。
那个叫苏倩的女人,是压垮我心中爱情神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是国家队最年轻的队医,
知性、专业、美丽,看向顾决的眼神里,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崇拜和爱慕。也是顾决的情人。
一开始,我并不知道。我只是单纯地觉得,这个苏医生,对我“关心”得有些过头了。
她会以“医学评估”的名义,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病房里。她从不问我感觉如何,
只是拿着一块平板,记录着我各项不断衰退的生理数据。她的眼神,不像医生在看病人,
更像一个屠夫在估量一头牲口的斤两。“林**,你的心肺功能衰竭速度,
比上个季度加快了百分之十二。”“林**,你的骨密度已经低于危险阈值,
任何轻微的碰撞都可能导致粉碎性骨折。”她总是用最平静的语气,陈述着最残忍的事实。
然后,她会状似无意地叹一口气,目光瞟向窗外正在训练的顾决。“顾决的压力太大了。
你知道吗,他每次看你受苦,晚上都会做噩梦。他的皮质醇水平一直很高,
这非常影响竞技状态。”“林**,我作为医生,说句不该说的话。爱一个人,
有时候是成全,是放手。”她像一把温柔的刀,一寸寸割开我用爱意编织的谎言。
她不是在劝我,她是在用最专业的角度,给我洗脑,让我相信,我的存在,
就是顾决唯一的弱点,我的死亡,才是对他最大的“成全”。我开始变得沉默,
整日整日地盯着天花板。顾决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,每次来,也只是匆匆地坐一会儿,
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安慰话。“晚晚,再坚持一下,等我拿了冠军,我们就什么都有了。
”他握着我的手,那双手曾经能给我带来力量和温暖,如今却只剩下冰冷的敷衍。
他的眼神飘忽,总是不自觉地看向门口,似乎在期待谁的出现。我知道,他在等苏倩。终于,
在一个深夜,我被一阵剧痛惊醒,挣扎着想去按床头的呼叫铃。病房的门虚掩着,
我听到了走廊里传来压抑的争吵声。是顾决和苏倩。“你到底还在犹豫什么?
”是苏倩的声音,尖锐而急切,“她这次的发作越来越频繁,这就是最好的机会!
只要我们停掉进口的特效药,换成普通的镇痛剂,她撑不过下一次大发作的!
到时候一切都会显得顺理成章,‘抢救无效’,谁也说不出什么!”我浑身的血液,
在那一刻瞬间凝固。我听到了顾决长长的、疲惫的叹息。“再等等,”他说,
“至少……至少等我拿到世界冠军。否则,我这二十年‘深情’的人设,不就白费了吗?
媒体会怎么写我?赞助商会怎么看我?苏倩,你懂不懂,林晚现在死,对我没好处。
她得死在我最荣耀的那一刻,那才是一场完美的谢幕,才能将我的价值最大化!
”“轰”的一声,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“爱情”的弦,彻底崩断。原来,我二十年的牺牲,
我视若生命的情感,在他眼里,不过是一场可以被利用、被最大化价值的“人设表演”。
连我的死亡,都要被他精心策划,成为他荣耀之路上,最悲壮、最感人的一块墓志铭。
我缩回手,没有再按呼叫铃。无边的黑暗里,我蜷缩在床上,
感受着身体和心脏同步传来的剧痛。我没有哭。因为我知道,眼泪,是对一个不值得的人,
最廉价的祭奠。从那一刻起,我心中那个为爱而生的林晚,已经死了。活下来的,
是一个只为复仇而存在的,来自地狱的恶鬼。3没人知道,我和顾诀并非天生的「共生体质」
。这世上没有那么玄妙的巧合,只有精心编织的爱与谎言。记忆回到二十年前,
那个阴雨连绵的下午。我和顾决都还是体弱多病的孩子,缩在孤儿院最不起眼的角落里。
我的遗传病已经初现端倪,时常发作的剧痛让我连走路都困难。而他,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
被医生断言活不过二十岁。我们是彼此唯一的慰藉,分享着一颗糖,也分担着对死亡的恐惧。
直到那天,我在院长办公室,看到了父母留下的遗物——一个尘封的金属箱。里面没有钱财,
只有一叠叠厚重的手稿和一台构造奇特的仪器。我的父母,是国内顶尖的生物科学家。
他们毕生的研究,就是这个名为“生命能量转移链接”的禁忌项目。手稿上,
父亲用清隽的字迹写着:链接一旦建立,宿主将承受双方所有的负向能量,
包括病痛、衰老;而受益者,则能汲取双方的生命力,获得超乎常人的健康与潜能。
这是一个疯狂的、违背伦理的构想。一个彻头彻尾的、单向的献祭。我抚摸着那冰冷的仪器,
看着窗外因为呼吸不畅而脸色发紫的顾决,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疯长。“阿决,”那天晚上,
我拉着他的手,躲在被子里,“如果有一种办法,能让你健健康康地活下去,你愿意吗?
”他黑亮的眼睛里满是渴望:“当然愿意!晚晚,我不想死,我想一直陪着你。
”我将仪器藏在床下,用我从手稿里学来的、半生不熟的知识,启动了它。
一阵尖锐的刺痛后,我看见顾决苍白的脸上,第一次浮现出健康的红晕。而我,
坠入了无边的痛楚深渊。我告诉他,我们是罕见的「共生体质」,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,
也是恩赐。他信了。从那天起,他成了孤儿院里最健康、最活泼的孩子,而我,
成了他身后那个永远病恹恹的影子。我看着他被游泳队教练选中,
看着他心脏的杂音奇迹般消失,看着他一路从市队游进省队,再到国家队。
每一次他潜入水中,我都感觉自己的生命力被抽走一分。每一次他站上领奖台,
我都在病床上,为他承受着双倍的病痛。我心甘情愿。可是,现在我想要收回这一切了。
4我的职业,是一名古籍修复师。这是我唯一没有被顾决的光环所笼罩的身份。这些年,
我拖着病体,只要稍有精力,就会沉浸在那些残破的故纸堆里。修复一本古籍,
如同与一位跨越千年的古人对话。你需要极度的耐心、精准的判断和对细节的绝对掌控。
这个职业,教会了我两件事:第一,任何看似牢不可破的链接,都有其脆弱的结点。第二,
最高明的修复,是看不出修复的痕迹。而最彻底的毁灭,则是在其最完整、最辉煌的时刻,
引爆它内里最致命的缺陷。我不再关注顾决的比赛,也不再理会苏倩的冷言冷语。那天下午,
苏倩又来了。她穿着一身挺括的白色制服,手里拿着惯用的平板电脑,
像一尊行走的人形精密仪器。她站在我的病床边,垂眸看着我,
语气是一贯的、掺杂着怜悯的专业。“林**,今天的气色看起来……很不错。
”她似乎有些意外。往常这个时候,我应该在病痛的折磨下脸色惨白,
连呼吸都带着细碎的痛吟。可今天,我只是平静地回望她,甚至对她露出了一个极淡的微笑。
“是吗。”我说,“大概是找到解脱的法子了。”苏倩眼底掠过一抹压抑不住的喜悦,
但她掩饰得很好,只是公式化地点点头。“你能想开,是最好的。顾决很快就要决赛了,
你的精神状态稳定,他也能更安心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在平板上划动,
嘴里念着一连串我早已麻木的医学术语。“骨密度持续下降,心率不齐……根据模型推演,
下一次大发作的临界点,很可能就在一周内。”她抬起眼,
像是在审视一件物品的最后保质期。“林**,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?比如,
想对顾决说些什么?我可以帮你转达。”我看着她那张写满虚伪和期待的脸,
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我摇了摇头,轻声说:“不用了。我想说的话,到时候,
他会亲耳听见的。”“而且,会听得……一清二楚。”苏倩的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,
她似乎觉得我的反应有些脱离她的剧本。但她最终还是将这归结于我临终前的回光返照。
她收起平板,公式化地嘱咐了几句,便转身离开了。在她走后,
我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张银行卡。那是顾决前几天托助理送来的,
里面是他带着施舍意味的生活费。他说:“晚晚,别省着花,想吃什么就买点,
别委屈了自己。”他或许以为,我的人生只剩下口腹之欲这点追求了。我用卡里的钱,
通过一个绝对保密的离岸渠道,联系上了一个人。5他叫张博文。是我父母当年的同事,
也是「生命能量转移链接」这个项目,除了我父母之外,唯一的知情人。父母意外去世后,
他因为无法接受项目背后巨大的伦理风险,主动退出,远赴海外,
成了一名低调的生物伦理学教授。我以一个求教的陌生学生的名义,给他发了一封邮件。
邮件里,我没有提顾决,更没有哭诉我的任何遭遇。我只是将我这些年,偷偷记录下来的,
关于我和顾决之间能量流动的详细数据,以及我身体各项机能衰退的医学报告,
全部整理成附件,匿名发给了他。在正文里,我只问了他三个问题。“教授,基于这些数据,
如果链接的『受体』突然被切断能量供给,同时『供体』积压的所有负面能量瞬间回流,
理论上会造成怎样的生理现象?”“这种回流,是缓慢的,还是瞬间爆发的?
”“造成的损伤,是可逆的,还是永久性的?”发送邮件后,我经历了三天漫长的等待。
那三天,我出奇的平静,甚至连遗传病的痛楚,都变得可以忍受。
我就像一个等待最终审判的囚徒,等待着那封决定他人生死状的信件。第三天深夜,
提示音响起。我收到了张教授的回信。信很长,字里行间,
他的语气充满了无法抑制的震惊和深切的不安。他显然已经猜到了我是谁。“孩子,
你到底想做什么?这种反向操作是极度危险的!我必须警告你,这无异于引爆一颗生物核弹!
”我的视线掠过他那些劝阻的文字,直接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。
“根据你的数据模型进行推演,能量的瞬间反噬,会在受体体内引发一场毁灭性的生理风暴。
它会瞬间摧毁他健康的生理平衡系统,让他体验到供体积压了二十年的所有痛苦的总和!
那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疼痛,而是指数级的叠加!”“这种爆发是毁灭性的,
造成的神经和器官损伤,将是……”我的指尖停在屏幕上,轻轻拂过那几个字。
【永久且不可逆的】。这就够了。我仿佛能看到顾决那张英俊的脸,在极致的痛苦中扭曲,
看到他引以为傲的健硕身躯,在泳池中痉挛、抽搐。他不是一直说,恨不得替我承受痛苦吗?
好啊。那我就成全他。我将他欠我的,连本带息,一次性,全部还给他。
我没有看完张教授后面那些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恳求。我平静地删除了邮件,
然后开始为我的复仇,做最后的布局。6复仇的蓝图,已经清晰。但我还需要一个保险。
我联系了一家以守口如瓶而闻名的瑞士律师事务所。视频通话那头,
是一位金发碧眼、表情严谨的律师。我以我母亲的名义,设立了一个死后触发的信托基金。
“林女士,请确认信托触发条件。”律师的声音通过电流传来,不带任何感情。“我的死亡。
”我平静地回答,“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死亡证明为准。”“请确认触发后需要执行的内容。
”“信托内的所有电子材料,将在我死亡确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,以加密邮件的形式,
分发给一个名单上的所有机构和个人。”那个名单里,
有全球排名前一百的所有媒体、国际体育仲裁法庭,
以及顾决背后每一个赞助商的品牌方法务部。而那些电子材料里,是我准备好的一切。
技术的完整研究报告、我这些年记录的能量转移数据、顾决和苏倩那些不堪入耳的通话录音,
还有他利用我健康的身体赚来的巨额财富的完整资金流向明细。律师确认完所有条款,
公式化地问道:“林女士,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?”我想了想。“有。”“请讲。
”“如果我没有死,这份信托将永久封存,永不启用。”律师那边沉默了几秒,
似乎在理解我这句前后矛盾的话。最终,他还是专业地点了点头:“好的,条款已备注。
”挂断通讯。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,玻璃上倒映出我苍白但平静的脸。我曾想,
如果我死了,那我就拖着他一起下地狱。让他身败名裂,被钉在体育史的耻辱柱上。但现在,
我有了更好的计划。死,太便宜他了。我要他活着。我要他活着,清醒地,用他自己的眼睛,
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云端的神坛,一步步坠落成一滩人人唾弃的烂泥。
我要他用他剩下的、充满无尽痛苦和折磨的漫长人生,来为我这被偷走的二十年,